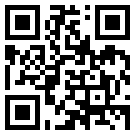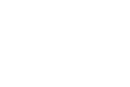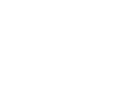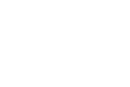Logomania,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一种对于品牌标识的狂热态度。尽管“品牌标识”作为一种品牌象征和家族徽章的转译,在时尚领域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Logomania文化则是现代时尚的产物。而它的诞生和发展,也清晰地勾勒出消费者与品牌文化日益紧密的共生历史。

1980年代,崛起于美国黑人社群的嘻哈文化,让慢慢的变多生活在底层的嘻哈艺术家迅速积累起财富。他们渴望通过消费,彰显自身的资本与社会地位。这一行为早在1899年,美国经济学家Thorstein Veblen就给出了确切的定义——“炫耀性消费”。
“ 炫耀性消费”成为了嘻哈艺术家们“武装自己”的核心理念:车子要选择最具辨识度的豪车,身上的首饰一定要是纯金的且要醒目张扬。嘻哈艺术家们的服装亦是如此,他们要衣服和豪车、金链子一样醒目,能够让人无需近距离观察便能清楚地知道他穿的是什么牌子的衣服。而装饰有品牌Logo的服装,毫无疑问对这些新贵有着无可拒绝的吸引力。
但彼时的欧洲的奢侈品牌尽管足够高贵,却没办法提供给他们想要的张扬。虽然Gucci、Louis Vuitton等奢侈品牌已经推出了有自己品牌标识的印花手袋,但他们要么没有开展自己的成衣业务,要么在设计上依旧维系着传统高级时装的经典语言。于是Dapper Dan,这个在嘻哈文化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赌徒”,便就此登上了时尚的舞台。
Dapper Dan原名Daniel Day,在1982年于纽约哈勒姆地区开设了自己的精品店,起初经营皮草服装生意。很快,他就注意到自己的主要顾客——嘻哈艺术家们的这一消费需求。他开始在自己浮夸的皮草大衣中加入奢侈品Logo元素,从Gucci和Louis Vuitton等奢侈品店里购买标志印花手袋,并将手袋拆解为一条一条的封边,装饰在大衣之上。随后,他又发现顾客们对这些印有名牌标识的服装单品需求愈发明确——他们更希望Logo可成为服装的主体。于是Dapper Dan购买了丝网印刷设备,将品牌的标识印刷在皮夹克等单品之上。他也会购买品牌的手袋,并巧妙地将其改造为服装。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说,Dapper Dan的设计是最早的“奢侈品民主化”实践,他让那些彼时高不可攀的奢侈品牌真正拥有了广泛的受众基础,也催生出了现代Logomania文化。

Dapper Dan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了品牌标识的力量,“它象征着地位和金钱,两者密不可分。重点是,你能拥有地位,但没人知道你没钱。所以,它才能在你的造型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尽管Dapper Dan的奢侈品民主化实践在1992年正式谢幕,但Logomania热潮却得到了延续。在整个1990年代,街头时尚和嘻哈文化影响力逐步扩大,成为了美式时尚的重要代表,知名设计师们纷纷围绕Logomania现象展开设计。譬如美国时装品牌Tommy Hilfiger就曾推出了一款由品牌蓝白红标识设计而来的抹胸上衣,当时的流行文化偶像如Destiny’s Child和Aaliyah都曾穿过这件单品进行舞台表演。


1999年,摄影师David LaChapelle受到Dapper Dan的启发,让嘻哈音乐人Lil Kim不着寸缕地出镜杂志拍摄,而在她的身上印满了Louis Vuitton的品牌Logo。这一创作无疑将Logomania文化推至了一种艺术表达的层面,后来许多音乐人和艺术家都对这张照片展开过致敬。

Logomania的诞生,就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表达力量,通过嘻哈文化对奢侈品最直白的引用,既呈现出了直观的炫耀性消费,也展现出了对一种流行文化的认同。

随着时装文化的发展,Logomania逐渐跳脱出了炫耀性消费的定义。在经历了1990年代先锋时装创作者们在设计中拥抱“挪用文化”的尝试之后,慢慢的变多的设计师意识到符号或者标识是可以被直接应用在创作之中的。2000年前后,时装界涌现出了许多以“改造”为主要风格的设计师,他们或是对日常之物进行全新的演绎,又或是将一些符号标识进行重新解读。这其中就包括西班牙设计师Miguel Adrover。

Miguel Adrover在1999年发布了个人品牌首个时装系列,他将彼时纽约街头随处可见的“I Love New York”文化衫通过重新设计转化为新的时装单品。到了2001秋冬系列,他更加大胆地将一件在Vintage商店里购买的Burberry风衣,通过反穿的方式塑造成了一条连衣裙,并将品牌标志性的格纹内衬和领标外露在大众眼前。

不难发现,Miguel Adrover的挪用对象很多元,从Polo Ralph Lauren的经典马球标识,到可口可乐、万宝路等大众消费品牌的标识,再到联合国这样社会机构的标识,他都以一种直白的方式呈现在了自己打造的系列里。对他而言,这种近似于Logomania的创作手法,表达的就是对消费主义的讽刺和对社会文化的关心。

在Miguel Adrover引发时尚行业争议的数十年后,来自格鲁吉亚的设计师Demna Gvasalia带着自己的品牌Vetements创造了同样的文化现象。他将DHL的标识转化为时装的一部分,用Champion、Juicy Couture、Fila等现成品牌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时装立场,并将Miguel Adrover未完成之事转化为了一种流行现象。


不过,Demna所做的并不仅只是挪用而已,他同样开始了“融合”的创作道路。在担任Balenciaga的品牌创意总监后,他将品牌的标识与不同的经典文化符号相融合并以印花的形式呈现在设计中。他会对万事达、可口可乐等品牌的原始Logo做改造创作,也会从《全美超模大赛》等流行文化符号中获得灵感,转变为新的设计表达。

Kim Jones同样也注意到了这种“融合”的力量。在这位英国设计师为Dior Men打造的多个时装系列中,他邀请了不同的合作对象来共同重塑Dior的经典Logo。这中间还包括了Shawn Stussy的经典手写字体,ERL品牌带有冲浪文化的符号,以及Stone Island罗盘标识的融入等。
这样融合创作的手法同样也出现在了其他时装设计师的作品当中。不同于Demna和Kim Jones在标识重塑上有着版权合理性,他们更多的是“挪用”后再融合。譬如Martine Rose将MTV的标识字体用在了自己的设计上,而尼日利亚设计师Mowalola则将《超级马里奥》的经典符号转变为自己的标识。在这里,Logomania变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符号之间的叠加,展现的更多是符号学上的解读空间,同时也彰显了创作者本身的文化立场。


顶级奢侈品牌们自然也注意到了这种标识叠加的商业经济价值。在2020年前后,不同奢侈品牌之间都展开了合作,譬如Fendi与Versace共同推出的Fendace系列,Gucci与Balenciaga共创的黑客实验室项目等。Logomania不再只是一种炫耀性的表达,更是成为了品牌文化传播的一部分。

随着时装商业化和民主化的不断推进,Logomania的身份也再度发生了变化,品牌标识开始以更艺术性的方式融入设计当中。不仅仅是Veronica Leoni,慢慢的变多的设计师愈发意识到,既然标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存在,那不如将其转化为一个独特的设计符号。


譬如在Diesel 2023秋冬系列的秀场上,设计师Glenn Martens将品牌的标识巧妙地转化为一件针织连衣裙。在此之后,这位来自比利时的时装设计师,在Diesel这个以牛仔著称的品牌中变本加厉地进行了标识的各种艺术化实践。D字Logo不仅被他用在了手袋设计之中,或直接转化为整个手袋的廓形,也应用在了各类服装设计之中。


在Raf Simons加入Prada之后,这位热爱青年文化的设计师同样意识到了品牌标识作为一个符号在时装设计中的重要性。他与Miuccia Prada联手,一同将品牌经典的三角形标识转译为更为直观的服装语言。在Prada 2022春夏男装系列中,三角形的标识或是被转化为手袋的廓形,或是作为拉链的设计出现在了衣服之上,还被制作成为戒指等配饰。而在Prada 2023秋冬男装系列中,三角图案标识又转化为了菱格纹的设计出现在了手袋之上。

Jonathan Anderson在Loewe担任创意总监期间,也将由他焕新的品牌标识作为一种时装表达。他不仅将Anagram标识转化为手袋设计的一部分,同时也将品牌的字母标识呈现在时装设计里。譬如在Loewe 2025春夏男装系列的秀场上,他就呈现了几件印有品牌标识的高领上衣,而这一设计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每一件衣服背后都会有的领标。
为什么如今的Logomania已不再似从前那般简单直接了?答案很简单,为吸引到更多人的注意。研究咨询公司Stylus的时尚主管Emily Gordon-Smith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传统标识和品牌(标识作为身份的象征)那种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特质,对当代年轻人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价值观截然不同,更喜欢对经典和传统的颠覆。”在互联网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当下,品牌标识以更为多元的形象呈现,不仅仅可以带给消费者新鲜感,还能更加进一步强化大众对于品牌的印象。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炫耀性消费的心理驱动,还是文化符号在流动中的挪用与融合,亦或是设计师们对品牌标识充满创造力的二次解读,当代Logomania精神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归属标记。
我们消费标识,同时也重塑标识。我们被品牌故事所影响,也同样用自身的解读去改写故事。这种动态而又充满张力的互动,不仅重新定义了消费文化,更折射出这个时代身份认同的流动性、文化创造的杂交性以及社会权力在编码与解码之间的持续博弈。这或许正是Logomania文化为咱们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启示:在符号的狂欢之下,涌动着的是关于我们自身存在方式的深刻对话。
,米兰体育app是免费的吗